勘探存在与对小说的勘探
——两个角度看米兰·昆德拉
作者补天灵石|来自作者博客
“勘探”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中的解释为查明矿藏分布情况,测定矿体的位置、形状、大小、成矿规律、岩石性质、地质构造等情况。一般说来,它的对象是矿产资源(金属、油气等)。这些资源业已存在,只是它们混杂埋藏于某些未知的不确定的地方。
因此,“勘探”这个词便具有了发现已存在物的未知或不确定方面之义,含有冒险之义。当文学资源(文体、文学主题等)作为勘探的对象,它的勘探者就具有了奠基者、先驱者的地位。正如荷马勘探了史诗,索福克勒斯勘探了悲剧,塞万提斯勘探了欧洲现代小说(假如可以这么说),荷马、索福克勒斯、塞万提斯便成了各自领域的奠基者、先驱者。
应该说,早在他们之前,史诗、悲剧、欧洲现代小说已经存在,只是当时这一体裁很不成熟,人们忽略了它们,毕竟给一种文学体裁命名乃后人之事。就像伟大的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在诗中所写:诗人没有创造出诗 / 诗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 很久以来它就在那里 / 诗人只是将它发现。荷马只是把史诗以一种较为成熟的、完满的形态展现给人们,后来人们继承了他的遗产,并以此为奠基,为样式,不断对之进行丰富、完善。于是,荷马就成了史诗的勘探者。
那么米兰·昆德拉呢?米兰·昆德拉勘探了存在与小说?正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写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在四个多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1]既然昆德拉本人都承认“存在”主题以及现代小说(昆德拉认为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揭开了欧洲现代小说的帷幕)在他之前已被勘探过,笔者还说米兰·昆德拉在勘探存在与勘探小说,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当然不是。我之所以选用“勘探”这一具有分量的词,有两方面含义:
一,米兰·昆德拉在已出版的十部小说中的确探究了“存在”之谜,揭示了“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同时他在小说观念以及创作实践上亦高度自觉,发现了小说的多种多种可能性;
二,表达笔者对米兰·昆德拉在以上两方面所做贡献的一种敬意。
米兰·昆德拉在勘探“存在”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第一部分说,“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2]他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变得“越来越盲目”, “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于是掉进了海德格尔所称的“对存在的遗忘”中。然而何谓存在?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并没有给存在下一个定义,而且还说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因此我们只能推断,存在是“一个关涉人和世界的本质的范畴”。[3]
昆德拉认为,自塞万提斯以来,欧洲四个世纪的小说以特有的方式,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
塞万提斯探讨了人的冒险,理查森审视了人内心的隐秘生活,巴尔扎克发现了历史环境对人的行动的影响,福楼拜探索了当时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托尔斯泰探寻了非理性如何作用于人的行为,普鲁斯特抓住了过去的瞬间,乔伊斯抓住了现在的瞬间,托马斯·曼探讨了神话对人的遥控,卡夫卡则揭示了现代世界的本质——官僚主义。
由此可见,昆德拉所认为的“存在”也是形而上的,模糊的,难以确定的。难怪他在与记者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的谈话中说到,“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4]作为一个小说家,昆德拉就是要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可能性。他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对活人的模拟,而是想象出来的人,是实验性的自我,是人的多种可能性。然而,人在世界中的可能性有哪些?在考察了卡夫卡、哈谢克、布洛赫之后,昆德拉总结出五种基本的可能:
K的可能性(绝对严肃地承认秩序,和权力同化,甚至与自己的刽子手产生默契)、帅克的可能性(绝对不严肃地模仿周围的世界,对权力拒不接受,把世界转化成一个唯一的、巨大的玩笑)、帕XXXXX夫的可能性(保守,顽固地怀抱已逝的旧价值不放)、埃施的可能性(盲从,无上帝时代的一种狂热)、胡格瑙的可能性(无道德律令约束的追求实际的为所欲为)。
这五种基本的可能性被昆德拉称为“五个方向标”,他在“五个方向标”的指引下,“在时空推移之后的新的人类场景中绘出了人的‘存在’的新版图,展示人的‘可能性’”。[5]可见,“可能性”构成了昆德拉斯考笔下人物的情境以及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没有‘可能性’这一维度,人就是机械的,别无选择的,一切都是规定好了的,只有一条路可走”。[6]可以说,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反思了“存在”(可能性在他那里获得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即人总是从可能性中来了解自身,因为他的存在还不是最后被规定的。人正是生活在诸种可能性之中,诸种可能性一起构成人的本质的最内在核心),而昆德拉则从小说学的意义上直抵“存在”。
昆德拉在迄今为止创作的十部小说中,创造出几十个人物(路德维克、泽马内克、露茜、马丁、伊丽莎白、爱德华、搭车男女、雅库布、伯特莱夫、露辛娜、雅罗米尔、米瑞克、塔米娜、特雷莎、萨比娜、托马斯、弗兰茨、阿涅丝、洛拉、贝蒂娜、鲁本斯、贝尔克、文森特、让-马克、尚塔尔、伊莱娜、约瑟夫等),这几十个人物并非现实中存在的,他们是昆德拉想象出来的,是小说家实验性的自我,是“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正如作者所言,“作者要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人物确实存在,无疑是愚蠢的。这些人物并非脱胎于母体,而是源于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句子或者某个关键场景”。[7]每个人物都有其“存在密码”,这些密码由一个或多个关键词支撑,这些关键词就是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维度。那么,昆德拉勘探的“存在”的可能性维度有哪些呢?
其一,个人在历史中的脆弱导致的价值崩溃。这是路德维克(《玩笑》的主要人物)的存在密码。路德维克原是布拉格一所大学的学生干部,爱开玩笑,在一次寄给女友玛凯塔的明信片上赌气地写下“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气。托洛茨基万岁!”一行字。在政治气氛过于严肃的时代,这个玩笑惹了大祸。路德维克被党组织审查,并被驱逐出党(他的好友,泽马内克,下届党组织主席,也参与了这一决定)。
在劳改期间,遇上露茜,精神受到鼓舞,但在渴求其肉体而不得的情况下赶走了她。劳改完后,他想借占有并污辱埃莱娜(泽马内克的妻子)的肉体报复泽马内克。然而,他欲占有的正是泽马内克所欲抛弃的(他不在乎埃莱娜,又找了一位年轻女友)。当一切明了后,路德维克被屈辱和羞愧压得喘不过气,只想“悄然一人躲到一边,把这段历史,这一场倒霉的玩笑抹掉,把埃莱娜和泽马内克抹掉,把前天、昨天、今天抹掉,把这一切统统抹掉”。[8]正如路德维克所思考的,“我不是自己个人历史的主体,而不过是它的客体,因而我也就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自我标榜的资本(我不承认折磨、悲哀、失败自身有什么价值)”。[9]个人在历史中的生活没有任何价值,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毁灭,“比专制远远广阔的毁灭,比我们所谓的现代的‘幻灭’要激进得多”。[10]也许在物质上,这个世界依然完好无损,但表面上的完整恰是毁灭的主要特征之一。
正如里卡尔所言,“生活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前进,仍然显得秩序井然……然而一切已经改变”。[11]庄严的历史在开玩笑。在事物与词语,生灵与面孔,行动与思想之间,产生了虚空——角状的冰淇淋变成了火炬的火焰,展现上天的石头天使宣告的只是虚空,粗俗的公民说教表演却带上了一种神圣仪式的沉重,温馨的明信片竟被当作政治宣言,连接它们的线条被截断了,一切都偏离了轨道。标准不再有,价值不再有,因为它们随时有可能转向自身的反面。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是陷阱,在陷阱中,为任何行动指定意义无异于自我欺骗,路德维克如此,“路德维克们”如此。
其二,追求绝对的青春时代的幼稚与邪恶。雅罗米尔无疑是最佳标本。他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温情与诗歌的浸泡中,始终充满激情与自我痴迷。在一次注视自己所画的挂在墙上的画时(画的下面写着他小时候所说的话),他被它们陶醉了,他觉得“被无数的自己所包围着,数不清的雅罗米尔充盈着整个房间,甚至充盈着整幢房子”。[12]这种自我痴迷与理想乐观,正是昆德拉所说的“抒情性”。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具有抒情性的人特指“那些对自己的灵魂感到痴迷,并渴望使之被听到的人”。[13]
在这一点上,贝蒂娜、洛拉同雅罗米尔是一致的。贝蒂娜在歌德死后把它们之间的情史公之于众,并出版成书,洛拉在流产之后带上墨镜(欲是掩饰悲哀,便越渴望体会到她的悲哀),这些举动都具有“抒情性”。但她们远没有雅罗米尔走得远。年轻的雅罗米尔以“被选中”的身份走进了社会。他追求爱情,数次进行性冒险;他崇敬离经叛道的艺术,公开批评他的画家老师;他背负社会责任,揭发女友的哥哥的叛逃阴谋。在完成揭发之后,雅罗米尔热血沸腾,并将进一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然而,不久之后,他“滑稽”地病死了。通过验罗米尔,昆德拉询问了“青春”的可能性(人人共有,或显现,或隐藏)。青春与革命是一对伴侣。年轻人从来不会怀疑青春赋予他们的巨大权力,因此他们会选择革命。而革命能带给人的,除了不幸,就是狂热。在这一点上,仵从巨教授的论述极其精彩:激情是有强度的;青春是无经验的;有强度的激情最具可能的维度是渴望绝对;当青春的无经验性与激情的绝对性结合并以主动性进入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革命年代”)时,它导致的可能之一是雅罗米尔的“恶”。[14]雅罗米尔是一个邪恶的人,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兰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15]
正因为这种青春的“恶”伴随着每一个人,随时有可能被激发出来,所以青春时代是可怕的。在《笑忘录》的第六部分,塔米娜在孩子岛遭到孩子们的虐待,投进一条河逃离,孩子们划着小船追上了她,看着她求救的痛苦的表情却只是笑着,直到塔米娜被水淹没。换言之,当处于青春时代的孩子们(他们思想狂热,头脑简单)投入“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便会制造出一种实实在在的灾难。19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红卫兵”事件便是这种灾难之一。昆德拉通过它的小说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这个共同的可能性。
其三,两极对立之间的不可调和。这其中包括多种对立:轻与重,灵与肉,媚俗与背叛,记忆与遗忘。
“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16]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开端,昆德拉就用哲思般的语言探讨了“轻与重”。托马斯是在轻重之间挣扎的典型人物。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医生的责任感、对特蕾莎的情感,构成了他沉重的生存境况,他为此感到步履维艰,生命几乎窒息。他竭力要逃离这种生命之“重”。当他拒绝在万人抗议书上签字,当他逃出对特蕾莎的爱去跟形形色色的情人做爱后,托马斯获得了生命之“轻”。重是残酷的,而轻便真的美丽吗?这种逃离“重”的“轻”依然让托马斯难以承受,他生活在进退维谷的境况之中。面对轻重的两难选择,托马斯痛苦地体验着,在“无数次轻与重的转换、冲击与选择之中,几乎耗尽了生命的全部能量”。[17]
终于,他选择了特蕾莎,回到乡村,远离了俗世尘嚣,生活在田园牧歌之中。但是,一场偶然的交通事故却将两个沉重而极富意义的生命顷刻之间带向了虚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重变成轻,轻变成重,重旋即又成了轻。在轻重转换之中,一切都飘向了虚空。然而,轻更好,还是重更好?昆德拉并没有回答,只是通过托马斯的死,向我们隐喻了人的生存困境。
爱德华、特蕾莎揭示了灵与肉的永恒对立。涉世不深的大学生爱德华一直梦想同时占有女友艾丽丝的灵与肉,即渴望灵与肉的和谐统一。但是,在宗教力量与政治权力面前,他妥协了。不信主的爱德华为性爱同信仰宗教的艾丽丝走进了教堂。当这一切被他无神论信仰的女上司发现后,为保住教职,爱德华又违心地用身体迎合了女上司的性需求。外界力量(如宗教、政治)的干预,宣告了爱德华只能生活在灵肉的痛苦对立中。特蕾莎也渴望灵肉合一。在少女时代,他就常常在镜子面前窥看自己,当她在镜子里看见另一个“我”的时候,便感到十分惊奇,竟不知此“我”只不过是肉体之“我”的复制品,而是以为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是灵魂在镜子中的身体上闪光。
这种渴望还可见证于她对母亲的灵与肉理念(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肉体集中营,一具具肉体彼此相像,而灵魂是根本看不见的)的拒不接受。特蕾莎尤其珍视生命中的“灵”,容不得灵魂的亵渎与堕落,灵肉一体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当她投入托马斯的怀抱后,托马斯的放荡(拥有众多情人,并与她们做爱)使她妒嫉、迷茫、恐惧。恶梦的反复出现便是她这种心理的最佳证明。在恶梦中,她被托马斯命令着和其他裸体女人一起在游泳池里唱歌、下跪,否则便会被开枪打死。特蕾莎再也承受不了这无尽的恐惧,她妥协了,开始寻找露水情人。她放弃了灵肉合一,开始捕捉肉体之爱的轻松与乐趣,渴望领会“爱情与做爱”的区别。最终她躺进萍水相逢的工程师的怀抱,与之疯狂做爱。对托马斯不忠的报复,却又使特蕾莎的灵魂恢复了知觉,再度回归到灵肉合一。不幸的是,特蕾莎在交通事故中丧失了生命,灵肉并没有如愿和谐交融。通过爱德华与特蕾莎的遭遇,昆德拉思考了灵与肉这一存在之谜,怀疑并否定了灵肉合一的可能,再次把人类存在的困境呈示出来。
“媚俗”概念的提出源于斯大林儿子雅科夫之死。英国士兵受不了雅科夫把战俘营的厕所弄得满是粪便,于是上报长官,而长官认为谈论粪便有损自己的尊严便不予理会,于是雅科夫扑向带高压电的铁丝网死去。“媚俗”这个词十九世纪中叶出现在慕尼黑,当时用来指“伟大的浪漫主义世纪细腻而令人作呕的余渣”;[18]后为布洛赫所用,代表最极端的美学病;1980年代被韩少功译入中国后,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在使用这个词。昆德拉在作品中如是解释媚俗的: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之为kitsch。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19]在这里,我们从人类学的层面理解: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对公众目光的绝对渴望,以至于自我的态度与行为蒙上了一层故意为之的姿态性。弗兰茨、贝蒂娜、贝尔克都是媚俗的标本。
弗兰茨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实生活,毅然踏上向泰柬边境“伟大的进军”之路;贝蒂娜在歌德死后,公布了歌德与她的情史,并成书出版;“政治舞蹈家”贝尔克热衷于在电视里抛头露面,不但在一次直播的“向艾滋病人献爱心”的活动中,滑稽地模仿议员杜贝尔克亲吻艾滋病人,还曾远赴非洲与那些快要饿死的、脸上盖满苍蝇的孩子合影留念。他们的如上行动逃不开渴望公众目光的虚荣。最终,由电影明星、流行歌手、语言学教授、医生、新闻记者、摄影师领导的“伟大的进军”居然变成了一场闹剧。和平、博爱、平等、自由、正义与进军者的虚荣划上了等号。更为可笑的是,在新闻照片中被解释为为泰柬人民的不幸泪水长流的女电影明星,其实是被法国语言学教授骂为“臭狗屎”之后屈辱的伤心。在大众媒体、摄影机遍地都是的今天,媚俗已强奸了真实。
在昆德拉笔下,背叛才是反抗媚俗的最佳途径。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比娜选择了背叛一切来反抗媚俗。她背叛了父亲,背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背叛了移民同胞的期望。“第一次的背叛是不可挽回的,它引起更多的背叛,如同连锁反应”,一次次地使她远离最初的背叛。在她眼里,有公众在场,考虑公众,就是活在谎言之中。“背叛甚至成为目的,成为萨比娜心中的‘美’”。[20]然而,一切背叛的尽头是空虚。萨比娜承受不了这空虚之“轻”,只能背叛自己原初的背叛;在疲惫的背叛之旅中又插进了媚俗。正如昆德拉所说,“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21]媚俗的不可战胜,背叛尽处的虚空,昆德拉又一次把我们带入存在的困境。
在谈到“遗忘”时,昆德拉既把它看作个人问题——“作为自我丧失的死亡”,也把它当作政治问题——“当一个大国要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它采取有组织的遗忘的方法”。 [22]无论是个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遗忘”总是对过去和历史来说的,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境况。米瑞克遗忘了(为保持自己的成熟形象与精神平衡,欲从女友那里取回“失落的信”,以便抹掉过去),雅库布遗忘了(他原谅了奥尔佳的父亲曾经对他的政治迫害并最终选择了移民),约瑟夫和伊莱娜遗忘了(约瑟夫不承认自己曾经的“坏小子”形象,并和伊莱娜一起选择了不回归),尚塔尔遗忘了(她后来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阿涅丝沉浸在回忆中(当她回忆起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时,才感到安慰和乐趣),但回忆也是遗忘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能记住的实在太少,遗忘的总是太多。然而,塔米娜却选择了记忆(她要尽最大努力取回落在布拉格婆婆家的信件与笔记,以留住对已死丈夫,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清醒记忆),不幸的是,塔米娜的记忆越发模糊,甚至几近消失,终于也陷入遗忘之中(去了孩子岛,被孩子们糟蹋而无动于衷,最后死在追寻过去的生命之河中)。遗忘是不公正的,因为“人们只会赞颂帕涅罗珀的痛苦,却不会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23]但遗忘又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只有不断地遗忘过去,才能“惬意”地生存在社会之中。
在以上的种种可能性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悲观与怀疑,这也许不是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但却是有可能发生的,是存在的可能性维度。至于如何摆脱这些存在困境,昆德拉并没有指出一条明路,他只是“存在的探究者”。在他所绘的存在之图中,为任何行动制定意义是可笑的,然而,生活还在继续,历史还在继续,昆德拉便走进了悖论:他也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求一种意义——拯救人与艺术,使它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但这个悖论是无法避免的,它也是我们的存在境况,昆德拉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
米兰·昆德拉在勘探小说
昆德拉不仅其小说中勘探了“存在”的重大主题,同时也审视了小说这门文学艺术,形成了独特的小说观念,并对这一文体进行了高度自觉独特的实践(笔者主要从这点进行论述)。这既可在他的三部理论随笔(《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和众多的访谈录、序跋中得到证实,也可见证于其创作的小说作品。
昆德拉曾两次定义小说:“小说就是以带有虚构人物的游戏为基础的长篇综合性散文。这些是小说的唯一限制。”[24] “小说是散文的伟大形式,作者通过一些实验性的自我(人物)透彻地审视存在的某些主题。”[25]视小说为散文的嬗变形式,昆德拉的这一观念很有代表性,它“表征了小说文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实进程”。[26]在这一进程中,小说要跨越19世纪美学强加于小说的义务与限制:建立在因果和时间关系链以及严格的情节与人物的等级化上的“一致性、真实性”和情节发展的连贯性;叙述的“同质性与统治性”(它一方面取消了其他所有话语,或者至少使得这些话语降为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抹去了小说家的声音或使之中性化,让小说家变成一个简单的叙述者);文本的“资料性”(它要求小说要忠实详细地描摹一个地方、一个时刻,也就是说要描摹一个合乎逻辑、能够辨认的社会历史环境)。[27]在这个层面上,昆德拉所要恢复的是福楼拜时代之前的小说天赋的自由,也就是要恢复那种挣脱了束缚和约定的小说精神与小说形式。因此,对偶然性的格外推崇,对插曲的偏爱,对复调形式的发展与创新,对数字的尤其重视,便构成了昆德拉小说景观的多道风景。
昆德拉首次提到“偶然”是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前两部分。在谈论托马斯和特蕾莎的爱情问题上,他使用了六个“偶然”,认为恰是这六个“偶然”把托马斯推到了特蕾莎身边,好像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东西在引导他。接着,昆德拉又指出:“我们不能指责小说,说被这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所迷惑……但我们有理由责备人类因为对这些偶然巧合视而不见,而剥夺了生命的美丽。”[28]至此,如果我们还不能清晰地洞见昆德拉对偶然性的推崇。在《不朽》中,这一事实变得更加清晰。《不朽》的第五部分的标题即为“偶然”,讲述了阿涅丝的一天。阿涅丝决心单独移居瑞士,这天下午她应该踏上返回巴黎的公路(她不喜欢晚上开车)。然而,很偶然地,她决定暂时不上车,先在阿尔卑斯山散一会儿步;晚上在高速公路上行了一段路后,她又很“偶然”地“开上一条不那么拥挤的公路”;又是很偶然地,就在这天夜晚,公路中央站着一个寻死的少女,当阿涅丝躲避时,车开进了沟里。阿涅丝就这样死了。一切都毫无征兆,因此,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念头都成了一种“极具价值的征兆”。而且,在《不朽》中,昆德拉借助“我”与阿弗纳琉斯教授的谈话,批判了小说“建立在情节和事件唯一的因果关系的连接上”的弊病。可见,昆德拉对“偶然”而非“必然”的推崇,显示了其小说美学的革命意识。
插曲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不喜欢插曲,因为插曲“不是在它之前的事的必然结果,又不产生任何效果,游离于故事这个因果链之外”,所以插曲可以省略,而“不至于使故事变得不可理解”。 [29]然而,昆德拉笔下的叙事不但不避免,还饶有兴致地大谈插曲。在他看来,如果省略了这些不主要的插曲,尽管情节得以连贯,而作品最为珍贵的思考空间却又可能受到损害,作品最主要的意义也会变得不可理解。《生活在别处》的第六部分“四十来岁的男人”的故事,是在雅罗米尔死后发生的,与他并没有什么联系,因而是一个插曲。但这个插曲和小说的主题形成了一种“关键的对位关系”,因此在诗人死去前叙述便具有了统一主题的作用。同样,《不朽》的第六部分(讲述鲁本斯与阿涅丝的故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第七部分(讲述托马斯与特蕾莎在乡下的生活),都是在人物死后进行的。它们对于理解人物的命运而言,没有什么必要性,但是,如果将其省略掉,这两部小说将会变成另一种模样,小说珍贵的思考空间也将大大缩减,因为作者在托马斯、特蕾莎、阿涅丝身上探究了“存在”之谜。因此,昆德拉补全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任何插曲决不会预先注定永远是插曲,因为每一件事,即使最无意义,都包含以后成为其他事件起因的可能性,一下子变成一个故事、一件冒险经历。[30]在这一点上,昆德拉小说美学的革命性又得以显现。
昆德拉小说美学的先进性在其对小说复调理论的发展与自我实践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复调”原是音乐术语。“音乐复调,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声部(旋律)同时展开,虽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却仍保留各自的独立性”。 [31]换言之,一方面,“各声部在节奏、重音、力度及曲调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各声部之间又彼此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 [32]而将“复调”引入小说理论,则源于巴赫金,他在其《诗学》一书中,着重强调的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 [33]可见,声音的多重性成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基础,也是理解其复调理论的关键。
昆德拉提到“复调小说”源于对布洛赫《梦游者》的第三部小说的分析。他说《梦游者》的第三部小说“由五个元素构成,由五条故意不同质的‘线索’构成”:一,建立在帕XXXXX夫、埃施、胡格瑙三个主要人物之上的小说叙述;二,关于汉娜·温德林的隐私式短篇小说;三,关于一家战地医院的报道;四,关于救世军中一个女孩的诗性叙述;五,探讨价值贬值问题的哲学随笔。尽管这些线索是“同时处理”的,也在不断地“交替出现”,但“并不真正联接在一起”,“复调意图并没有得到实现”。 [34]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分析后,昆德拉认为布洛赫的“复调”要更具革命性。《群魔》的三条线索虽然特点不同,但同属于小说故事,而《梦游者》的第三部小说的五条线索的种类彻底不同:小说、短篇小说、新闻报道、诗歌、哲学随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昆德拉所认可的“复调小说”的特点之一便是小说中包含的文类多样化。但是仅有文类的多样化还不能算真正的“复调小说”。昆德拉借用音乐术语,认为还应做到声部的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起简单的陪衬作用。[35]《梦游者》的第三部小说的复调缺陷就在于五个声部的不平等。它的第一条线索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享有“特权”,从而将其他四条线索减缩为陪衬。同时,将第二条线索和第五条线索“拿掉”,也无损于小说的主体表达。因此各线索的平等及整体的不可分也是昆德拉小说复调观的特点,这里的“整体的不可分”指各线索统一于同一个主题,在昆德拉这里则统一于“存在”之思。
《笑忘录》第三部分“天使们”包含五种文类:小说故事、自传性叙述、评论性随笔、寓言故事、诗意叙述。这五种文类各自独立,且共同探讨了“天使是什么”的主题。《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第六部分“伟大的进军”包含的线索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关(斯大林儿子的故事、神学思考、亚洲的一个政治事件、弗兰茨在曼谷遇难的故事、托马斯在波希米亚下葬),之所以能联在一起,主体的统一性起了关键作用(它们共同揭示了“媚俗”的意义)。应该说,昆德拉对小说文类复调的标举及创作实践,既遵循了小说艺术的内在逻辑,也映现了当代小说写作的跨体写作潮流。
昆德拉小说复调实践的又一个特点是作者自我与小说人物关系的崭新处理,即作者的不隐身。这种“作者的不隐身”多次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生活在别处》用“我不得不说,这个女人冲雅罗米尔弯下身子的样子时那么温柔残酷”、“我们叙述的第一部差不多包含了雅罗米尔十五年的生活”等宣告了作者自我的高调介入。在《爱德华与上帝》、《笑忘录》、《不朽》、《慢》、《身份》中,都出现了“我”、“我们”,这里的“我”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甚至全盘操控着小说叙述的整体局面。通过身份上的确认,这个“我”便是小说家本人——米兰·昆德拉。他并不介意自己的介入,甚至把自我的地位提到了小说人物之上。这种主人公与作者地位的不平等的小说,按照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不能列为“复调小说”。然而,昆德拉对自我与主人公关系的崭新处理,是服务于小说的主体表达的。自我介入的功能之一是在小说故事“表面的差异内部建立一种‘声音’上的稳定性或持续性” ,[36]从而使小说具有整体统一性。在此意义上,小说家自我的介入增强了昆德拉小说的复调性。
昆德拉小说复调实践的再一特点是,梦境叙述与现实叙述的共时并存。梦是一种无意识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不真实性。而在昆德拉笔下,“梦的世界并不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或更不真实,更有意义或更无意义”。 [37]他的小说尽量避免使梦在任何意义上从属于所谓的现实叙述,而是让二者具有共时性。《生活在别处》的第二部分“克萨维尔”完全是雅罗米尔的一个梦,我们开始并不知晓,并以为它与主人公的故事共时并存,直到最后一部分,才得知真相:雅罗米尔梦想成为克萨维尔一样的人物。而在《笑忘录》的第六部分、《慢》以及《身份》的最后几个章节,这个特点尤为明显。塔米娜上了拉斐尔的车远离小城,来到神秘的孩子岛,开始了既是“女王”,又是“囚犯”的生活,但终因恐惧逃离,溺水而死。这是梦,还是现实?塔米娜是否真的死了?我们难以确认。唯一确定的是,“某种界限被穿越了”,两个世界同时融而为一。在《身份》中,梦境与现实更难以辨认。正如作者自问:“谁梦见了这个故事?谁想象出来的?是她吗?他吗?他们两人?……从哪一刻起他们的真实生活变成了这凶险恶毒的奇思异想?……究竟是在那一刻,真是变成了不真实,现实变成了梦?当时的边界在哪里?”[38]连作者都陷入了疑问,我们又从何而知呢?小说《慢》更是将想象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放在一个“魔盒”中。
小说家与他的妻子薇拉在法国乡村的城堡旅馆过了一夜,在这一夜中,作者虚构的两个故事同时上演(当代的:关于文森特和他的同类;古代的:关于T夫人与青年骑士),其间由于当代的故事太过喧闹,以致薇拉被闹醒两次。第二天早晨,在自己汽车里的小说家和薇拉,与骑着摩托车的文森特、坐在马车里的青年骑士在城堡的停车场上交会了。现实性和非现实性,都在神秘中得到了交换。对梦境的叙述与对现实的叙述,在昆德拉的小说XXXXX时进行,它们并存于小说构筑的整体空间中,犹如两个平等的声部,彼此独立,相互补充,完美地呈示了共同的主题。这种复调元素又给昆德拉的小说景观增添了亮点。
对数字的格外关注,是昆德拉小说中体现出的一个客观特点,也是昆德拉小说创作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在读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昆德拉的整套作品后,我们能发现他的每一部作品的章节编号非常明显,这与作者的一贯追求有关:将小说分为若干部分,将各个部分分成若干章节,再将各个章节分成若干段落。[39]显然,昆德拉希望借助以明确的数字标注小说的章节的方式达到使小说环节清晰的目的。笔者认为,昆德拉的这一做法还有另外的意图,即清晰地凸显其小说的音乐性。他从小受到音乐的熏陶,并跟随一位有名的音乐老师学习音乐,这也影响到昆德拉日后的小说创作。他把他所创作的小说的每一部分、每一章节分得特别清楚,并把小说的每个部分比作一个乐章,每个章节比作一个节拍,由于各乐章的长度与其所包含的章节数量以及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时间之间比例的不等,从而将小说的各个部分标上一种音乐标记,如中速、急板、柔板等。以《生活在别处》为例:
第一部分:诗人诞生(1-76),76页,11章节,76/11,中速
第二部分:克萨维尔(77-114),38页,14章节,38/14,小快板
第三部分:诗人自赎(115-206),92页,28章节,92/28,快板
第四部分:诗人在奔跑(207-246),40页,25章节,40/25,极快
第五部分:诗人嫉妒了(247-350),104页,11章节,104/11,中速(这不同于前四部分,因为它的速度还受制于本部分叙述事件的真实时间——104页只叙述了雅罗米尔一年的生活时间,与第一部分——75页叙述了雅罗米尔15年的时光相比,这是一种慢镜头,因此为中速。)
第六部分:四十来岁的男人(351-382),32页,17章节,32/17,柔板(与第五部分的情况相同,32页只叙述了几小时之内的事情,因此速度极慢。)
第七部分:诗人死去(383-416),34页,23章节,34/23,急板
当然,不同的音乐标记,取决于各乐章所欲呈示的主题。如中速的平静舒缓,快板的兴奋紧张,急板的刺激,这种情感氛围与主题的展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一点,有论者已作过精彩的分析。[40]昆德拉不仅在小说中注入音乐性元素,同时这种音乐性也不落俗套。在他看来,一部交响乐或者一首奏鸣曲的乐章顺序有其规则,即缓慢的乐章与快速的乐章、悲哀的乐章与欢乐的乐章交替出现,[41]这种情感的反差形成一种俗套,而在《生活在别处》(把它比作一首奏鸣曲,七部分为七个乐章)中,各乐章的顺序为“慢、快、快、快、慢、慢、快”。二、三部分都是“快”的乐章,气氛却有兴奋与苦闷之分,五、六部分同为“慢”的乐章,气氛亦有和谐与悲悯之分。可见,昆德拉的“快”并非都意味着情感的欢快,“慢”也并非都意味着情感的悲愁,而且快乐章与快乐章相连,慢乐章与慢乐章相连,别出心裁地应用于小说中,的确是一种创新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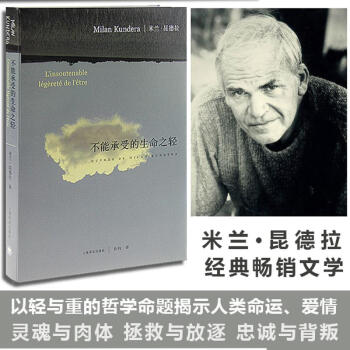
对数字的偏爱,也可体现于昆德拉作品的结构。他的作品多由七部分组成,《玩笑》包括七部分,《好笑的爱》由十部小说删为七部,《生活在别处》由六部分增为七部分,《笑忘录》七部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由六部分拆为七部分,《不朽》七部分,《小说的艺术》七部分,《帷幕》七部分。众多之“七”显示出昆德拉对“七部分”结构的迷恋。尽管他一直否认对神奇数字“七”的迷信,也不认为这出于理性的计算,而只是说它来自一种“深层的、无意识的、无法理解的必然要求”,无法避免。但我们知道,昆德拉从小深受音乐教益,尤其喜欢巴赫和贝多芬的复调音乐作品(它们的结构也多是七部分)。长期浸润在这种氛围中,必然会受到影响,也许他正是从这种“七章架构的形式自恋中找到了音乐学上的依据”。 [42]但我们无法否认,昆德拉作品的七部分架构模式是其小说观的独特之处。
当然,昆德拉的小说理论以及小说文本的美学特点,还有很多值得研究探讨,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结语
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并没有止笔,还在继续他的“存在”之思,“小说”之思,但他已经通过丰富的作品勘探了“存在”的可能性维度,亦勘探了小说艺术的可能性维度。正是他在以上两方面的杰出建树,使他成为当代最具声望的小说家之一。
注释:
[1]5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2]4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3] 425页,周国平,载于《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李凤亮、李艳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1
[4]54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5] 21页,《“城堡”与“迷宫”——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论集》,仵从巨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9
[6]327页,《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吴晓东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8
[7]《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8]337页,《玩笑》,米兰·昆德拉著,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6
[9]147页,《玩笑》,米兰·昆德拉著,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6
[10] 386页,《关于毁灭的小说》,弗朗索瓦·里卡尔,载《玩笑》,米兰·昆德拉著,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6
[11] 388页,《关于毁灭的小说》,弗朗索瓦·里卡尔,载《玩笑》,米兰·昆德拉著,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6
[12]22页,《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著,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3]113页,《帷幕》,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
[14]6页,《“城堡”与“迷宫”——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论集》,仵从巨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9
[15] 136页,《〈生活在别处〉英文版序言》,景凯旋译,载于《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艾晓明编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2
[16]6页,《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17]139页,《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仵从巨主编,华夏出版社,2005.2
[18]66页,《帷幕》,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
[19]295页,《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20]9页,《“城堡”与“迷宫”——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论集》,仵从巨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9
[21]305页,《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22]144页,《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艾晓明编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2
[23]8页,《无知》,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24] 142页,《〈笑忘书〉英文版后记——菲利普·罗思与〈笑忘书〉作者的对话》,载于《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艾晓明编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2
[25]182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26]263页,《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李凤亮著,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
[27]116页,《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弗朗索瓦·里卡尔著,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28]43页,《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29]337页,《不朽》,米兰·昆德拉著,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0]338-339页,《不朽》,米兰·昆德拉著,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1]92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32]41-42页,《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李凤亮著,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
[33]43页,《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李凤亮著,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
[34]92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35]95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36]158页,《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弗朗索瓦·里卡尔著,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37]132页,《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弗朗索瓦·里卡尔著,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38]189页,《身份》,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
[39]109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40]参见《“城堡”与“迷宫”——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论集》35-38页,仵从巨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9
[41]112页,《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
[42]72页,《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李凤亮著,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
近代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在学理上的标志,是一种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例如自由、平等、博爱,它开创了“口号政治”的先河,它试图实现某些不真实的、不可能实际上实现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并号召人民为实现这样的乌托邦而轻视当下生活和生命中的“平凡琐事”,它鼓动人们把当下生活的价值系于未来某种理想状态的实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性的哲学与文学,「开始着力分析描述人的私人性而非公共性,并且渐渐放弃追求自身之外的永恒价值」,“抓住瞬间的美好”精辟地概括了这种新启蒙精神。

今晚9点,社科院著名学者尚杰老师继续为我们开讲《确定性的丧失:20世纪新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六讲:“宏大叙事”与“转瞬即逝的美好”。尚老师将通过理论和实例,分析上述思想演变的过程。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报名参与。
下载地址
此书籍由mobi图书网书友分享,如果您喜欢该资源,请支持并购买正版,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电脑端】azw3、mobi、txt等格式推荐使用稻壳阅读器阅读
【手机端】可使用番茄小说等支持mobi、pdf、txt格式的APP
【注意】手机端仅kindle阅读APP支持azw3格式,建议转换格式再用手机浏览。






留言评论
暂无留言